前面已经说过,旧社会灭亡时,会给新社会留下一笔遗产。这笔遗产不仅表现在民俗、习惯、经济生活和政治结构等有形的方面,更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尺度,传统的道德标准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等等无形的领域中,其中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关心程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把它叫作“政治态度”。所谓“政治态度”,是指国民对国家的治理所应有的性质抱有的一种普遍概念,比如国家应该怎么治理,由谁治理,统治者有什么权利,该不该受到限制;被统治者应不应服从,服从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条件下服从,以及被统抬者在统治者的压迫或过度统治下是否应该反抗等等。在历史的发展中,国民的“政治态度”往往有很大影响,可以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式和速度。在英国,经过许多次的反复较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形成某种平衡,双方都逐步学会在这种平衡或称一定限度中行事。
A.“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英国人最自豪的是他们的“自由”,他们自称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en)。这是他们世代相袭的光荣称号, 就象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在英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几乎都以“自由”为口号, 它的旗帜上必然写上“自由”一词。“自由”意味着反对压迫,反对暴政,反对侵犯人民的权利,尽管它听起来有时显得空泛抽象,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又确实有具体的内容。
“自由”最早是在贵族与国王的斗争中确立的。
和封建时期的整个欧洲一样,英国贵族一开始就处在与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但英国的王权从最初就比其他国家强一些。这是由于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时(1066 年),把土地划成极小块让贵族封授,并结成“索尔兹伯里盟”所造成的。在相对有力的王权下,贵族们尽管时常反叛,发动内战,但力量终不足以撼动王权,使英国分裂成无数的小国。因此英国贵族对国王的斗争,时常不是为争取各自“独立”,而是为争取“最高权利”。他们不愿让国王有丝毫的“越权”,而竭力维持在王权所及范围内的最远的离心地位。
由于这个情况,英国贵族与国王的斗争, 除造成事实上国家的割裂局面,却也还留下一些积极的因素。一方面,由于王权的相对有力,使国家始终没有分崩离析;另一方面,贵族的反抗又给王权加上某种限制,确定了“统治者”(国王)和“被统治者”(贵族)之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个范围内,谁都不应当超越界限 。
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是英国贵族的“自由”。贵族对国王的斗争,留下两项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大宪章和议会。1215 年的“大宪章”是在诸侯拥兵逼迫下由国王约翰签署的,其中最重要的几条规定说:国王在没有征得贵族同意时不可随意收取贡赋,也不能任意向臣民勒索财款;“若不经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令我等群起攻之,肆行讨伐。”条文还规定说,假如国王违背诺言,贵族就有权拿起武器驱除暴君,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都应站在起义者这一边。显然,“大宪章”是贵族对王权的重大脏利,它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贵族以外的其他阶级。但它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王的权力不应是无限的,它应受到某种制约,国王应该在法律的控制之下行使职责。虽然后来在“长期议会”时人们对“大宪章”作了后世人的解释,使它在内涵上发生质变,但它反对王权专制的含意,却极有价值。
议会初时,是国王向各地派捐税的协商会,并没有反对王权的用意。当然,在“大宪章”制定后,国王就不得任意征税了,他必须和各地去“商议”,“议会” 这个名称就出于法语的“商议”一词,本是协商征税的意思。议会后来成为反对王权的政治中心,这是最初召集议会的国王们所未及预料的。但国王一开始就把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交给议会——让它去批准国家的赋税,这就难免不在后来发展成对国家财政的全面控制。此外,英国的议会又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三级会议”不同,在三级会议中,三个等级三分天下,这就使贵族的势力始终占上风,而贵族因与国王有太多的共同利害,便很容易听国王摆布,特别是后来,当王极强大,民族国家建立起来时更是这样。英国的议会则把贵族和僧侣都归于一院,让它去和下院中人数众多的下层骑士与平民相对阵,这至少在数量上就形成劣势。此外,国王又把 上下院作为一个整体摆在和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上,去和它
们“商议”征税。这样做,显然就带有议会和国王平位的含义。所以当后来民族与王权对抗时,民族掌握着现成的反抗工具。
英国贵族对国王的争权就这样盖上了“自由”的印记。尽管在当时贵族们只是为保护封建特权而战,但他们的斗争却仿佛带有全民族的性质, 为后来反对专制王权提供了现成的先例。既然贵族对国王的胜利以“大宪章”的形式保留下来,那么一切平民反对派就很容易为自己找到历史的依据。“为自由而战”的口号可以为一切阶级所用, 而各自赋予它独特的阶级定义。贵族们在封建时期为维护封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被后世热烈地赞美着,“自由”这个词抽象起来,深深地扎根在世世代代英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他们对历史的骄傲和对未来的希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就是这样诞生的。
英国贵族尽管在历史上留下过一点功绩, 但他们在中古时期的主要作用却仍然是使国家分裂。一个贵族在自己的庄园领地上有绝对的权力, 成为国家不能统一,经济不能发展的割据势力,不消灭他们,民族不足以强盛。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的分裂势力,是在诸侯的自相残杀中灭绝的,这场混战就是红白玫瑰战 争(1455-1485)。由于两个王室争夺王位,把全国大大小小的旧贵族世家全都卷了进去。战争的结 果是这些世家全部覆灭,王位落到亨利·都铎手里。他娶约克家的女子为妻,使分裂的国家重归统一。 这以后,旧贵族没有了,专制王权得以建立,都铎 王朝在完成统一的任务中取得统治委任权,它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英格兰正式出现。
紧接着由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父女共同完成了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任务。亨利八世因离婚案发动宗教改革,割断了英国教会对罗马教廷的依附关系,从而解除了欧洲天主教强国——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对英国独立的潜在威胁。从此后,由于信仰不同,英国民族就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一个天主教国王的统治,民族国家得而在宗教改革的大动荡中诞生。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不仅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达成民族的空前团结,而且在1588 年消灭入侵的“无敌舰队”,取得了对当时唯一可以威胁英国民族生存的国家——西班牙的彻底胜利。民族国家保住了,英国第一次作为欧洲大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B. “君权神授”:失去委任的专制王权都铎王朝是十分幸运的:当它完成了这两项伟大的民族任务——统一和创建民族国家后,它自己就因谱系中断,而让位给苏格兰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由于这两项丰功伟绩,它的统治得到举国的拥戴,尽管它十分专制,容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但它的功绩掩盖了它的缺陷,它在专制王权最终确立的那一霎那离开历史舞台,让它的继承者去面对全民族的挑战。
一个统治者如果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的统治具有合法性,那他的统治就失去存在的道理了。斯图亚特的国王们就是这种人,他们只信奉一个原则,这就是“君权无限”。为维护这个原则,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乃至去冒天下之大不韙。为了给君主的绝对权力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提出“君权神授”。但是象“君权神授”这样一种论点,就连地位比他们稳得多的都铎王朝的君主都是不敢公开表达的,詹姆士一世却摆出一副神学家的派头说:他的权力来自上天。他不喜欢议会说三道四,就对议会说:“我不愿人们辩论我的权力。”但他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民族不是把他看成统一和民族国家的继承人,才承认他的存在吗?詹姆士不理解这一点,从这时起,国王和议会就开始交恶了。
如果说那铎王朝因完成统一和创建民族国家而取得统治委任权,那么斯图亚特王朝只有继续保持这两项成果才能巩固地位。但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对这一点一窍不通,在他们统治的四十年中,这两项成果又都好象成问题了,到头来眼看都要保不住。
英国的民族国家是在对天主教作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反天主教实际是英国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但詹姆士和查理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都对天主教过份宽容,甚至当天主教徒要杀害国王、颠覆政府时,詹姆士都无动于衷,不肯实施惩罚性法令。这就是 1605 年“火药阴谋
案”败露后发生的事,詹姆士首次与民族情结严重对立。接着,他又和西班牙议和。西班牙大使甚至成了他的心腹谋臣;他还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查理去向西班牙公主求婚,联姻不成,反受到西班牙的奚落,大伤了英国人民的感情。后来,查理登位后为雪求婚受辱之耻,向西班牙开仗,均告失败。查理本来是可以借民族的情绪提高他在国民中的地位的,但他却坚决 不承认议会有讨论国事的权力,因此得不到议会的拨款,只得在兵败丢脸的情况下收兵作罢,为维护“君权神授”的信条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很显然,斯图亚特的专制王朝不再能代表民族了,王权失去了它的第一个统治委任权。
同样地,詹姆士和查理很快地破坏了都铎朝时的民族团结,使国家再次陷于深刻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君权神授”论使国王和议会不能合作,强行征税又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反抗。他们的宗教政策更使全民族截然分成两个阵营,为民族的分裂创造了条件。詹姆士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因而竭力维护英国国教中最接近天主教的那些规定。但这种做法极大地触犯了他的清教臣民, 因为清教所要求的,正是取消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成份。这样,为了“君权神授”,国王再次和人民对立。查理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仅让法国出身的王后在宫廷中公开恢复天主教,而且起用国教中最亲罗马教会的一批人掌管国教。1633 年这批人的首领劳德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宗教的最高官员,这把国教中最温和的反对派都驱赶到清教一边去了, 这以后,两个阵营就正式形成。1637 年,劳德在查理示意下要把英国祈祷书强行推行到信奉长老会教的苏格兰,以此为导火线引起英国革
命。1642 年 8 月, 查理终于不能靠合法的手段制服议会,于是在诺丁汉向议会宣战 。内战爆发了, 国家正式分裂了,斯图亚特王朝交回了第二个统治委任权——它的国王亲手挑起了内战。
现在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统治委任权”。统治委任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需要、人民的意志。历史的需要总是由人民的意志来体现的,因为人民是物质生产的直接从事者,他们的意志直接来源于物质利益的需要。当一种政权形式出现时,是因为这种形式有存在的理由,它的出现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这种形式完成它的使命但又无法容纳历史进步新的要求时,它的存在就成为社会继续前进的阻力,因而迟早要变还。这时候国民的“政治观念”就起作用了,人民能不能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愿不愿为此而坚决斗争?统治者肯不肯倾听人民的呼声?对人民的意志作什么反应?对这些挑战的回答,决定着一个民族未来历史的走向和命运。
我们并不说某种政权形式就绝对地好,或绝对地坏,我们认为它的出现是有某种合理性的, 但一旦这种形式失去了统治委任权,它无论如何总是要消失的,只不过消失的时间可能有迟早,消失的途径可能不相同而已。对一个民族来说,失去统治委任权的政权形式消失得越早,民族的苦难就越少。英国克服专制王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C. 从内战到复辟:一个循环英国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一路领先,始终和它的人民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有关。有人说英国民族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民族,这一点也不夸张。它的人民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掌握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英国人的政治观念。正因为这样,它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民族。后来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把英国的强盛和突飞猛进分别归结于种种自然的、地理的、经济的因素,仿佛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由它的人民去创造,而是由大自然恩赐似的,这些人,为什么不去问一问:他自己的民族为什么落后呢?
专制王权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英国人反抗王权的斗争就开始了。伊丽莎白刚领导英国战胜无敌舰队,国王和议会就开始冲突,议会开始反对专卖权。专卖权对王室来说,是一项很好的经济收入,国主靠出售专卖权,既可以充实国库,又可以控制工商业,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专制对民族却是一个赘瘤,它使工商业停滞,没有创新精神,又使商品昂贵,剥尽民间财力。一个对王权有百利而对民族无一利的制度,立刻在议会受到攻击。伊丽莎白后期的几届议会,每一届都提出反对专卖权。1601 年的议会情绪尤其激烈,当王室专员在议会宣读专卖品的清单时,一个议员大声发
问:“是不是面包也要专卖?”立刻引起哄堂大笑。伊丽莎白知道众怒不可犯,就及时退让,避免了矛盾激化。
伊丽莎白这样做是很典型的都铎时代的统治方法。都铎王朝君主总是走一步看一步,试探性地伸出一只脚,若是没有反应,再向前走一步;如果遇到抵抗,就会立刻缩回。都铎王朝的君主很知道照顾国民情绪,在他们统治时,英国只有荣誉, 没有耻辱。伊丽莎白甚至为保持民族团结始终不结婚,这也使她赢得了无数英国公众的爱戴。
斯图亚特的国王们却决不愿向民众的意志屈服。詹姆士一上台就宣布“君权神授”,立刻引起强烈反对,以后的每一届议会,都要在议会权力问题上与国王发生尖锐冲突,国王则用尽一切威胁、利诱、恐吓的办法,不惜使用逮捕、判刑等手段 ,企图制服议会。发展到后来,就是不召集议会,实行无议会的专制统治。
国王的这些恐怖手段如果是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议会也许早就不作声了;但在“生而自由”的英国,却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628 年召开的议会使冲突发展到白炽的程度,当时查理一世在战场上打败,急切地需要新的军费。议会本是愿意为战胜西班牙而动员国家拨款的,但它提出一个条
件,即承认议会的传统权利。议会的要求以《权利请愿书》的形式公布,它一共只有四条,除两条是应当务之急对士兵宿营和戒严条例提出指责外,最主要的内容则重复“大宪章”的原则:不经法律审判不得关押臣民;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赋税。查理一世因为急等钱用便认可了《权利请愿书》,但当第二年议会要他照《权利请愿书》的规定行事时,他却反悔前言,命令解散议会。议员们群情激愤,在国王的传令官到达之前赶紧把门关上,派人抵在门后,同时,匆忙间通过三项决议:凡是想输入天主教者,或建议征收未经议会许可的捐税, 或“自愿”交纳这种捐税的人,统统是国家的敌人,也是自由的敌人。议长不肯通过这项决议,便离开座位起身要走。激动的议员们把议长拉回来, 硬把他按在座位上,强行唱票,通过了以上决议。事实很清楚,英国人是不允许国王胡作非为的。
1629 年议会解散后,查理一世就再也不召集议会,他开始强迫征税,对公开的抗拒进行坚决镇压。议会的反对派领袖全都被捕入狱。不久,他又开始大量出售专卖权,还开征荒唐的新税——船税。这些就已经足以使英格兰鼎沸了。但他还不满足,在宗教问题上的专横拔扈使最温和的反对派都离开了他。于是革命爆发了。
在长期议会召开时,议会绝没有反叛的意思,议会虽然处决了为人民所痛恨的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但并设有对国王的权力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主权的主张。这时的长期议会,和以往几次议会一样,只是在要求议会的权利。议会甚至在制定《大抗议书》时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大抗议书》仅以 11票多数获胜。查理的悲剧是:他始终不认识人民的意志,不懂得统治的决窍在不违背民意。他以为议会的分歧给了他天赐的机会,1642 年 1 月 4 日,他对议会动武了。他带领几百个武装扈从闯进议会,要逮捕议会反对派领袖。是国王先向人民开战,于是人民才站出来保卫议会。伦敦的武装市民把议会首领接进城去, 议会也转移到伦敦市政厅开会。查理诀定向整个民族宣战,1 月 10 日,他离开伦敦;8 月,他在诺丁汉城堡上向议会宣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还有什么选择余地呢?他们只好拿起武器。国王既然以武力来对付人民,人民只好用武力来回敬。但一个用武力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的政权,是不配继续存在下去的,推翻国王、树立议会主权的思想,只有到这时才会萌生。
议会主权的思想就这样在内战中形成了。国王放弃了政权,唯一可以取代他的就是议会。内战期间,议会征收捐税,组织军队、指导战争,用它的各个委员会负责处理王国事务,成了真正的政府。这说明,国王在英国已经是多余的,国家没有国王也能生存。1649 年 1 月,当国王被彻底战胜时,议会通过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权力 ”这是
议会正式宣布它的最高主权。这个原则确立后,尽 管后来有许多曲折,但英国的历史就一直向这个方 向发展。直到今天,议会仍然是英国政治权力的基 石。另一方面,就连反对议会的人也不能不接受议会的原则。1642 年查理在向议会宣战时发表的公告中说:“我的愿望是,用已知的本国法律统治国家, 我在上帝鉴临之下,郑重而真诚地宣誓,我要维护议会的正当特权和自由 。”假如查理早一点说出这样的话,他又何需发动内战?但正是内战的需要迫使他说出这样的话。“君权神授”从这一刻起就彻底地破产了,内战刚刚开始,专制王权已经失败。
1660 年 4 月,查理一世的儿子在荷兰布列达发表宣言,答应给国家带来秩序,给各集团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5 月,他被国民会议迎立回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
D.“光荣革命”:未来社会的基石查理二世复辟后,王权和议会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1661 年召开的议会虽然以强烈的保皇情绪著称,因而有“骑士议会”的美号,但议会 在内战中的胜利又使国王和“骑士”都不会忘记。 正象研究英国革命史的权威学者希尔所说:“政府和下院的关系本身就是个矛盾 尽管下议员们本人都是保王派,他们却能充分地利用几十年的变迁为他们争得的新的宪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议会和国王都靠复辟过活,它们的利益本应该一致,但双方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这说明无论历史如何曲折,英国的王权专制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查理恢复专制的手段段比较隐蔽,但方向 却一直坚定不移。他不再和议会整体对阵,而是和他所称为的“老友”——保守的乡绅和国教徒结盟。但同时查理又从来不甘心受他们的制约,因此他在 1670 年和法国的路易十四缔结密盟(多佛条约),答应在条件成熟时就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 以此换取法国的津贴,以便在危难时得到法国的帮助。查理这样做正和他的祖辈投靠西班牙一样,是为王权的私利而拿民族的利益做交易。这时的法国
是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也最有可能干涉英国内政。但查理做的时候非常谨慎,多佛条约一直保密;直到临死前他接受忏悔时才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由于查理的心计,他临死时几乎就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了:他已经击垮了议会反对派辉格党,差不多牢靠地控制着议会,他还把中央的权力伸进各个市镇,让市镇团的选举听命于国王的支配。他的权力比他的两位祖先都大,在他的统治下,几乎就要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君主专制。
继位的詹姆士二世比查理更崇拜专制,但他不象查理那样隐晦。他在查理弥留之际就公开向法国大使大献殷勤,登位后,又公开向路易十四表示道歉,说他没有征得路易的许可就召开了议会, 而本来他应该向路易十四请示一切的。他摘去与乡绅——国教合作的假面具,认为恢复专制的唯一依靠力量是天主教。他因此任命天主教军官,建立天主教军队,在全国宣布信教自由,强迫英国国教会宣读信教自由令。这样,托利党被迫和辉格党联合起来了,奥伦治的威廉应两党之邀在英国登陆。经过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战斗,夺取了詹姆士的王位, 这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从血统上说,王位的新主人是詹姆士的女儿和女婿,这样就保留了斯图亚特的族谱,但王位的内容却因此起了变化。
根据议会条件,威廉接受“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中除宣称常备军为非法这一条外,所有的条款都是“自古就有的权利”,比如定期召集议会,议会言论自由,国家的赋税由议会决定,国民有请愿的权利等等。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条款,关键是:是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服从议会的法律。如果不是议会的选择,这个国王本是不能取得王位的。反过来说,议会既可以缔造国王,也可以废除国王,议会成了国家的主权,议会的权力终于确立了。在光荣革命中,不仅专制的王权被消灭,连独立的王权也消失了;从今后,国王附属于议会,而不是议会附属于国王。一个人统治国家的时代过去了,在以后的年岁里,统治国家的将是议会——它虽然还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却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由国家最有势力和最富有的人组成。个人专制结束了,英国完成了从绝对王权向多元寡头制的转化,国家经济起飞的第三个政治条件具备了,光荣革命是未来社会的基石。不久后,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将这一点更明确地宣布出来:它的“兵变法”(1689年)使议会控制了军权;它的“三年法”(1694年)规定议会任期三年,而每隔三年又必须召开一次新的议会;它的“叛逆法”(1696年)使国王不能够对反对派任意加罪;它的“继承法”(1701年)更是明确地规定了王位继承者的顺序,把所有信奉主教、困而有可能依靠外国势力、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人统统排除在外。这样,议会把国王置于它自己之下,英国的王位架空了。
光荣革命的影响还不只于此。英国人突然发现,为时20 年之久的革命和流了大量鲜血的内战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问题, 竟被光荣革命轻而易举地解快了。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并不是因为它不流血(事实上是流了少量的血),而在它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改变了政权的性质。从表面上看,政权一点也没有变,国主依然在,虽说换了人,却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传统得以延续,历史没有割断,英国仍是君主国,国王仍是国家的最高元首。然而,权力的结构起了变化,国王和议会交换了位置,一个人的专制让位给一批人的共同执政。在这批人中,平衡和相互牵制将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必要前提。这些变化看起来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国王和议会达成协议:议会让国王当国王,国王则同意让议会凌驾于自己之
上。这就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权力结构可以在不改变政权形式的前提下加以改变,而这样做的条件是:在被统治者的坚决要求下,统治者作出适时让 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从光荣革命中学到许多东西,在统治者看来,光荣革命靠妥协而避免了革命;在人民看来,革命的威胁可以逼迫统治者退让。洛克的政治学说正是对这种经验的总结。他说:假如政府违反契约,对人民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拿起武器,以暴力抵抗暴力。但暴力的抵抗只能是最后的手段,人民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在事情还来得及收拾时更换立法机构,设立新政府。坚持人民有暴力抵抗的权利,正是防止发生暴力革命的最好手段,因为“防止祸害的最好方式是向那些最容易走向祸害的人指出这样做的危险和不公正。”这以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革命,光荣革命成了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革命。英国人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改革和渐进成了英国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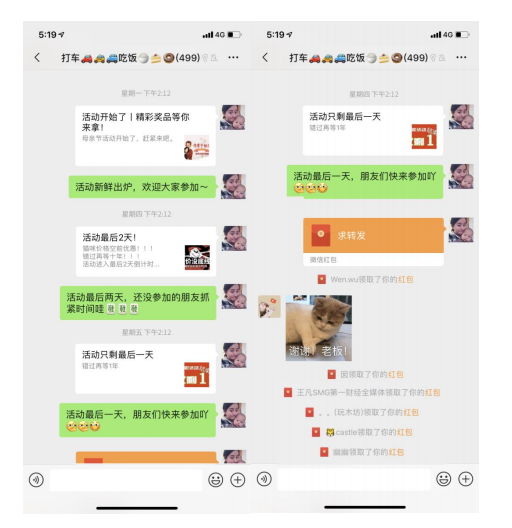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