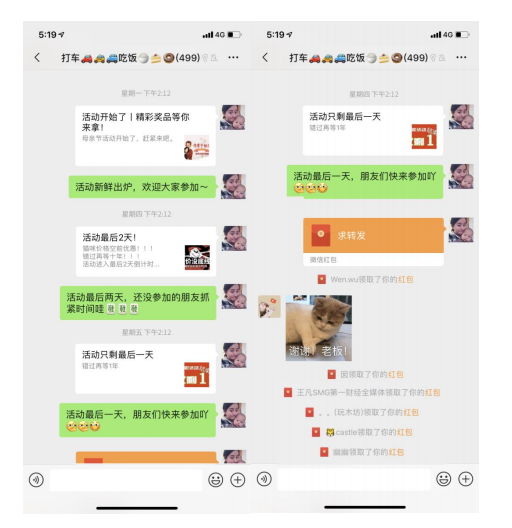2003年2月15日是周六,欧洲发生了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1),抗议即将对伊拉克发动的 战争。在伦敦,估计有100万人涌上特拉法加广 场,挤满从泰晤士堤到欧斯顿火车站的街道;巴塞 罗那和罗马有100万人游行,米兰有60万。50万人 无畏于刺骨的寒冷,聚在柏林的提尔公园,几乎与 该市夏季举行的爱情大游行(Love Parade)人数 相当。每一处聚集的人群都是和平的。有一些人被 逮捕,但没有暴力。参与示威的人形形色色:有一 些皮装打扮的未成年人,还有披着巴勒斯坦式头巾 或身着无政府主义标志性黑衣的青年,他们看起来 不那么面善;但绝大多数穿着暖和的冬季外套和时 髦的鞋子,他们是可敬的市民——退休老人、中年 学者、工会成员、高中生和大学生。有许多示威者 举家出动,父母和祖父母自60年代以来头一次参加 游行,孩子们在人生中首度体验政治示威中愉悦和 艰苦相杂的独特感受。一份德国报纸称此事件 为“普通人的起义”。
很多示威者带着横幅和标语牌,有些是组织者提供的,其他是自制的,宣告了他们走上街头的各种动机:“巴勒斯坦自由”,“不要为石油流血”,“疯狂牛仔病可以休矣”,“美国,真正的流氓国家”,“泡茶不打仗”,还有(我个人最爱的)“别再有这种事”(2)。不像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没有人对被宣战方抱有任何同情;没有伊拉克国旗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相片。对大部分人,真正的焦点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战争是否是答案。73岁的托马斯·埃利奥特,一位来自埃塞克斯郡巴西尔登区的退休律师,解释他为何来参加这次也是他人生首次的政治示威:“我记得战争,”他告诉一名记者,“和轰炸在伦敦造成的后果。战争手段只有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柏林当地一所高中的两名同班同学——14岁的尤迪特
·罗德和里卡达·林德纳,对有人来问她们为什么游行感到惊讶。“战争,”她们说,“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位支持和平的游行者——77岁的老兵希尔德·维塔舍克补充道:“解放柏林时我们已经
历过战争——不要再有了,绝不再要战争(niewieder Krieg)。”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当你的视线扫过外头的人山人海,看到最多的往往是单写一个不字的标语牌。
一些观察家视2月15日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前法国内阁大臣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宣称,一个新的“欧洲国家”(3)已在那天诞生。数月
后,在一篇原标题为“2月15日:是什么联合了欧洲人”的文章中,两位欧洲知名学者于尔根·哈伯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呼吁欧洲人“制衡美国在国际舞台
和联合国中的霸权主义单边政策”(4)。如施特劳斯-卡恩、哈伯马斯和德里达论称,欧洲对美国军事主义的抵制可为欧洲人创造出新的自我认同,而这一认同最首要的基础是将弃绝战争立为国家政策的纲领。
就在大规模示威前10天的2月5日,出版了一本罗伯特·卡根的著述:《天堂与权威: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Order)。卡根曾短暂地效力于里根政府,较早就开始提倡用美国的实力在全球散播民主,是最早力
促对伊拉克开战的一批人之一。这本著作很快就跻身畅销书行列,其基础是一篇名为《权威与软弱》(“Power and Weakness”)的文章,出现在
2002年春季的一份相当不起眼的期刊《政策审议》(Policy Review)上。卡根试图借用不久前一本关于性别差异的书的标题来概括欧洲和美国的差
异:“在主要战略和国际问题上,”(5)他宣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大西洋两岸的纷争不仅是欧洲人反对某个单一事件的结果,也不仅是反对美国政府某些特殊政策的结果。“是时候停止虚伪了,”卡根写道,“假装欧洲人和美国人共有相同的世界观,甚至假装他们共有同一个世界。”欧洲人已对权威背过身去,宁可活在后历史(posthistorical)的天堂中;美国人则认识到真正的世界霸权和军事实力仍然不可或缺。“造成大西洋两岸间鸿沟的原因,深埋在长久以来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卡根的分析,如哈伯马斯和德里达对新欧洲认同的呼吁那样,折射出伊拉克战争在大西洋两岸所点燃的辩论火光。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重新审视这些争辩。但现在,以上内容已足以让人明白,在三者笔下,欧洲人和美国人差异的核心是什么:21世纪之初,认可暴力是解决国际争端必要手段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多得多。2003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6),询问在特定状况下战争是否为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被调查的美国人当中有55%的人强烈同意。而在法国和德国只有12%的人持同样观点。
21世纪初的欧洲有强大的经济,但对把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兴趣寥寥。欧洲各国用经济、文化和法律的实力影响世界,用它们处理各国关系和处理国家与公民关系时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和体制来影响世界。相反,美国以军事基地、盟约和协议所编织成的巨大、紧密的全球网络,来推行真正的全球影响和霸权。美国已成为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Garton Ash)所说的“最后一个真正的主权欧洲民族国家”(7)。发动战争的能力和意愿是独立主权国家的传统必备要素,而这一传统已发生了改变。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至少在欧洲是如何发生的,就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