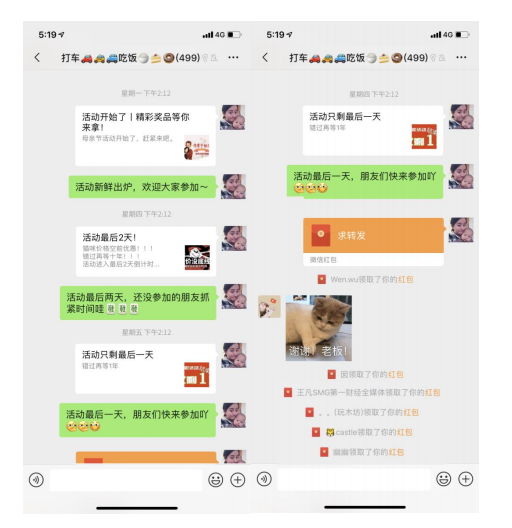GLM600数字超声波探伤仪
2019-07-14 阅读:306
我们往往觉得柏林是个军事文化比较突出的城市, 但军事元素在维也纳一样常见(5), 衣着光鲜的部队穿行街道是那里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 甚至连赞美基督圣体的圣体节( Corpus Christi) 这样极为宗教性的节日, 都有让教会、 王室和军方增进彼此感情的欢宴。 19、20世纪之交的相片上, 哈布斯堡王室家族的男性成员皆着军服, 沿着排有士兵的街道, 跟着圣礼队伍行进。军方代表国家, 在法兰西共和国也一样, 尽管政府时常与军队搞僵。 1871年, 在法国败给德国并签署《法兰克福条约》 GE600数字超声波探伤仪后不久, 年迈的麦克马洪元帅带领120,000人行军穿过朗香平原进入巴黎,在人山人海的观众发出的欢呼声中拥抱了新政体下的平民代表, 以此承诺军方支持共和。 自1880年起, 共和国将巴士底日——7月14日——设为国庆节, 会在朗香平原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作为庆祝, 后来这样的阅兵在每个能摆出守备队夸耀一番的法国城镇都会进行。 1894年, 在沙特尔市检阅部队的总统卡西米尔- 佩里耶( Casimir-Perier) 赞颂道“军队, 这爱国主义的伟大学校” (6)。 虽然欧洲各国军事机构的公共职能不一而足, 可各国的军队都是卡西米尔- 佩里耶所说的“国家形象” (7)的化身——或者, 更准确地说, 是国家理想形象的化身。
每座欧洲大城市的脉络中都织入了国家的战争回忆。 当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50—60年代重建起巴黎城, 他用战役的名称给几条街道起了名——他
伯父在1806年的耶拿(8)对普鲁士的辉煌胜利, 还有他自己的军队在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9)和1859年马真塔(10)的两次不光彩的表现。 每座都城都有胜利的纪念物: 伦敦特拉法GE600数字超声波探伤仪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柱, 颂扬1805年英国对法国的海战大捷; 巴黎的凯旋门, 始于拿破仑位于其权势顶峰的1806年, 作为其伟大军队( Grand Army) 的纪念; 柏林的凯旋柱, 建于1869—1873年, 标志着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成就。
国民英雄的坟墓点缀着每一座都城: 从圣保罗那朴素的威灵顿花岗石棺, 到黄金半圆顶的荣军院的地下室里华丽的拿破仑安眠地。 除了这些国家的
圣灵殿, 还有千百个更平凡的凭吊地标示着国家的军事史: 普鲁士各个城镇中简单的纪念碑缅怀着阵亡于色当或克尼格雷茨的当地人, 远离尘嚣的苏格兰村落的小教堂墙上的饰板镌刻着在帝国某些遥远边陲死去之人的名字。 军事属于伟业和霸者, 宏伟且遥远, 但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熟悉又亲近。每个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GE600数字超声波探伤仪同体, 因为国家太庞大、 太复杂, 无法直接触摸。 正因如此, 如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提醒我们的那样, 一个国家“必须人格化后才能被看见, 象征化后才能被爱戴, 想象化后才能被感知” (11)。 欧洲各国一直都必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来构成其公民的政治想象。 20世纪之初,这些象征和记忆有显著的军事烙印。 国家最希望用来自我定义的, 是能够带来胜利、 熬过失败的英雄主义、 自我牺牲和使命感。 戎装男子给国家存续所依赖的美德赋予人格, 陆海军给国家的铁纪和团结赋予象征。 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 20世纪早期的国家就无法存在——事实上, 甚至无法存在于想象。这就是为何每个国家, 无论多么弱小, 都有自己的
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