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箱根,举行了一次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中心议题是日本和现代化,讨论的成果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1965 年所编著的《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一书的第一章。箱根会议可以说是国际上第一次认真而又系统地讨论关于现代化的问题。这次会议为“现代化”概念立下了八条标准:
1.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
2.较高程度的无生命动力能源的利用,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
3.社会成员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以及通过这一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程度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
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性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
6.一个延展和渗透的大众传播系统。
7.存在大规模的诸如政府、商业、工业等社会制度,以及成长中的这些制度的官僚管理组织。
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和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
这八条标准与后来的学者们为现代化概念所做的种种概括相比,相对地说较为简单。箱根会议之后,现代化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现代化理论在当时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英国前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有关的。1960年,围绕着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国内出现了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使日美关系趋向紧张。在这种情形下,赖肖尔受命于肯尼迪政府,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由于赖肖尔出生在日本并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又是哈佛大学首屈一指的日本史专家,并且参与过美国国务院对东亚政策的制订,这三重背景使得赖肖尔成为在日本人看来可以接受的人。1961 年,赖肖尔保留着哈佛燕京学社主任的头衔来到日本,被誉为“学者大使”。他不断地在日本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日本的“现代化”。实际上赖肖尔关于日本现代化的观点早在哈佛东亚系教书时就形成了。1957 年 8 月,赖肖尔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站在转折点上的亚洲政策》的文章,提出:“尽管人口过剩和缺少天然的资源,但日本自十九世纪以来仍然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世界的强国。”他把日本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作了比较, 认为中日两国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决定了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采取了西方的模式,比中国先进了一个阶段,而这种社会结构又是由一个社会的传统所形成的,“现代”只能从“传统”中来。赖肖尔与当时的哈佛东亚系主任费正清合写过一本很有名气的讨论中国和日本的传统的书:《东亚,伟大的传统》于 1960 年出版。赖肖尔的日本“现代化”理论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日本学术界对日本的“传统”和“现代”问题的广泛探讨。但赖肖尔本人在当时并没有给现代化下过什么精确的定义,按照他自己发表在 1965 年 1 月号日本《自由》杂志上的《什么是现代比》一文的说法:现代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重要的变化,他认为,现代化的内容和意义还不明确,但正因为这一点,它才成为“还没有定义而实际上却存在着的现象的一个方便的名称。”
当然,赖肖尔的到来并不是促成日本学术界关于现代化讨论的唯一因素。日本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这一方面的讨论,例如政治学家腊山正道在1950 年代初就写过三卷《近代国家论》。在赖肖尔出使日本之前,日本已经掀起了一股关于传统、民族意识和社会结构方面的讨论高潮。但不夸张地说,这次高潮也是由一个美国人促成的。1946年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出版了她的那本名噪一时的综合性著作:《菊与剑》。这本书从日本传统、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强调了日本由传统而形成的国民特性,日本价值观念与西方的不同,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对日本这个民族所产生的诸如自杀性进攻、剖腹自杀等种种不理解。本尼迪克特的书被译成日文后,对战后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连日本人也认为,日本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关于民族性及社会传统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本书所引起的,直到今天,日本学者们仍不断地提到这本书。《菊与剑》也成为美国政府在战后制订对日政策的依据之一,在美国的亚洲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由于本尼迪克特影响的存在,箱根会议的召开再加上赖肖尔来到日本后多次提到现代化问题,促使这场关于日本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在六十年代风靡了全日本。战后日本政治学鼻祖之一、东京大学政治系的丸山真男在 1961 年编辑出版了《现代的人与政治》;历史学家福田恒存则从1963 年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他的《日本近代化试论》;时至今日日本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家象丸山真男、中根千枝和土居建郎等人仍在继续探讨传统、现代化和国民性特征这些课题。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促成日本进行关于传统和现代化讨论的并不是外来因素,而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整个民族对自己在战时行为的检讨,进而成为对历史和现状的再思考。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国的监督下进行了较彻底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军事系统方面的改革)。到了 1960 年前后,日本发生了“经济奇迹”,又一次崛起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到底是哪些原因促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飞速发展,然后走上了极端的法西斯道路,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又在战后十几年中再度崛起?这一切一直成为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心议题,也使现代化成为这些中心议题里最引人注目的基本理论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象日本一样经历了百年来的痛苦 经历和后来的飞跃发展,并同样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巨大影响,西德的学术界到了七十年代也掀起了探讨现代化理论的高潮。
然而,在日本所出现的这场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反过来又影响着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我们尚不能断定日本的讨论在什么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但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因为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大量关于现代化研究的文献,特别是美国的文献,许多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并且还有不少著作把日本与中国和俄国等国家进行比较。例如普林斯顿的詹森除了编著前面提及的《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一书外, 在 1969 年还著有《对现代日本早期制度史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克沃特·鲁斯托在 1964 年与罗伯特·华尔合著了《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 华尔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 1963年第 4 期上发表过“日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一文。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豪特和约翰·特纳在《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一书中则将日本、中国、英国、法国作为范例研究从早期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六十年 代还出版了规模庞大的《日本现代化研究》系列丛书,而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则在1960 和 1970年代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政治现代化》丛书。哈佛的几位东亚问题权威费正清、赖肖尔和后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的阿尔伯 特·克雷格也是现代化讨论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1965 年合著了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书:《东亚, 现代的转变》,集中探讨了日本与中国走向现代化时的不同历程。赖肖尔自己在 1966 年结束了大使生涯后,于 1972 年还写了一本很有名气的书:《美国与日本》。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热津斯基也以日本近现代为题,于 1972 年写了《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机与变化》。不过,在关于日本现代化的讨论方面最有影响的书恐怕还是稍后一些在1975 年由普林斯顿的欧洲史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西里尔·布莱克所主编、集普林斯顿、哈佛和康乃尔等校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诸领域八位教授之力合写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项比 较研究》。
当然,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是从 1960 年以后,也不是从对日本的兴趣开始的。从所接触到的国外文献来看,我们已很难断定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具体年代,因为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并没有花精力追溯它的起源。英语中早就存在着 modern(现代)这个词,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学家们一直
把君士坦丁堡自 1453 年陷落之后的历史称之为“现代史”,用以将他们的时代与他们称之为的“黑暗中世纪” 区别开来。今天西方国家在使用modern 这一词时,在意义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们认为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把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至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而将十月革命以后的时代称之为现代,用以强调资本主义的没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1949 年之后的中国学者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了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做这种意义的区别,虽然他们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做了一些阶段的划分,但他们在使用 modern 这一词说明历史进程时,仍包括着我们现在所说的近代和现代两个时代。也许他们在最初使用“现代化”时,只是从“现代”这一词的无意识延伸,或者只是有意识地用以指新近的东西和新近的历史进程等。考察“现代化”这一词作为术语的起源对我们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这一概念所包容的社会变动与历史过程。不过可以指出,至少在1932 年以前就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因为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尼在 1932 年于伦敦出版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力》一书中就已经写道:“现代化”是一种“通用却又意义不明的表达”。同时我们还至少可以举出,1960 年以前就有人使用“传统”与“现代”的观点,或者用现代化理论写了一些关于现代化方面的书和文章。例如费正清 1948 年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中就提出了“两个中国”的看法:即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普林斯顿的社会学教授、后来成为东亚系主任的小马里恩·利维在1949 年则出版了《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一书,1953 年又写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中的相反因素”一文,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 1958 年所写的《传统社会的消逝, 中东的现代过程》更是一本极其有名的现代化理论专著。不过,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所出版的文献来看,现代化研究形成高潮肯定是在 1960 年之后, 并且美国是这一研究的主要推动者。
美国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目标所以主要集中 在亚洲和第三世界,是与战后的世界形势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关。战后,苏联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和西方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以致于政界的领袖们惊呼: 共产主义的“铁幕”和“竹幕”分别降临于欧洲和亚洲。紧接着美国又在朝鲜打了一场至少是美国人认为并没有获胜的战争,同时在五十年代亚非拉国
家又掀起了解放和独立运动,这一切都使得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订自己的政策 ,修改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策的基点,而具有远见的决策的形成又仰仗于对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基础研究。冷战开始后,美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所谓新月形地带周围的国家, 以便加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遏制。到了1960 年前后,冷战达到了高潮,对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研究也同样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在地区性研究中美国却特别重视东亚与苏联。从统计数据看,在1946 年至 1970 年之间,仅仅关于中国的研究美国政府就资助了 1,500万美元,私人基金会则提供得更多,单是福特基金会在同一时期里就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了 2,680万美元。从 1945 年到 1970
年,用西方语言和俄语写就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博士论文共为2,817篇,其中美国竟为 1,401篇! 以致于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系的查默斯·詹森教授评论说: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简直飘在钱海里”。在美国学者看来,西欧和北美各国近代以来国内的历史进程是比较平稳的,而苏联和亚洲许多国家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历了大起大落。
与亚洲许多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个国家是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外唯一未发生革命而
又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因此将日本作为范例与亚洲别的国家进行对比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至少可以总结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比较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哪些条件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时起码应具备的。如果这些经验能够普遍化,当然会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富有指导意义。但要用一个确切的概念从理论上诠释这种普遍的进程远非易事, 现实总是比理论所能包含的内容丰富得多,而这一进程又确确实实存在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许多学者使用了“现代化” 的概念。虽然我们并不排除美国的一些学者们在使用现代化概念时含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的味道,并且有些人也确为美国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和对东亚的扩张政策进行辩护,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些学者们的探讨还是持严肃认真态度的。
除了世界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外政策的修订对现代化研究有推动作用外,五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现代化研究出现高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正象自然科学在这一段时间里不断地从学科边缘衍生出新领域一样,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也不断地在学科内日益精细化, 在学科外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许多学科甚至已与自然科学交织在一起,很难划出明显
的边界。现代化研究从方法上来说正是一种这样的跨学科项目。事实上,社会科学的发展业已证明: 利用单独一门学科的知识来解析较大的社会问题已经难以胜任,跨学科的方法才更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从许多专业的社会科学家都探讨现代化问题这一点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化研究横越了许多领域,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不过因果关系是这样的:这些学科在五十年代以来产生的革命性变革促成了现代化研究的深入。
哈佛的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曾在芝加哥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今日伟大思想》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为题,概括和分析了战后社会科学的重大变化和发展,介绍了卡尔·多伊奇等人所评判出来的从 1900 年至1965 年社会科学中62项“创造性成就”。贝尔认为,这些成就的突破性进展和完成主要在战后时期。但我们这里所想略为论及的不是社会科学的成就,而是研究方法的变革,特别是战后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比较研究方法的风行。诚然,上述几个学科中方法的变革并不限于比较方法,并且比较方法的使用也不是战后才开始,例如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当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计
量方法,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比较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路克和霍特 1938 年所写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 1930 年代则已是闻名遐迩的比较历史学者。但战后比较研究的兴起在方法论上却具有着变革性的意义,它深受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而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通过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而得出结论,而是更注重于从抽象的角度比较对象的结构功能,以追求富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在政治学中,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大卫·伊斯顿1953年发表了被誉为政治学中具有“革命性”的著作:《政治系统》,开创性地从结构功能角度研究政治制度。
1956 年,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也从系统和结构观点出发,利用比较研究发表了《比较政治制度》一文,提出了英美式、前工业社会式、专制主义式和欧洲大陆式的四种政治制度模式,在这之后,从结构功能角度研究政治制度或系统的比较政治学著作涌如潮水。进入六十年代后,博士研究生们所撰写的比较政治学方面的博士论文比政治学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多,由此可见一斑。以致阿尔蒙德和宾格汉·帕威尔在 1966 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关于发展的研究》一书中毫不
夸张地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比较政治学研究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其实不仅是政治学,还有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在战后也都出现了这股以结构功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浪潮。这一方法与来自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揉合在一起, 显然能够弥补只具有历时态性的单一研究方法的不足。比较方法的兴起和研究对象的抽象化,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围的日益扩大,需要得出的结论更加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科学发展本身愈来愈要求精确化和定量化。作为一种横向领域的现代化研究正是在上述形势下达到高潮的,它正好需要运用比较手段将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化为一种共时态进程,在比较研究中建立普遍化的模式。
如果我们仅仅把现代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待,恐怕还不能说明这个命题的全部。有趣的是,几乎就在箱根会议和现代化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相继提出要在本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目标。理论与实践的摸索, 能如此同步,如此丝丝入扣,原因何在?当不得而知。但发展中国家普通表现的对现代化的热望则无疑深化了现代化研究,并使它在六、七十年代中在西方和整个世界的社会科学界中历时不衰。例如在
1962-1964年,以斯坦福的社会学教授阿历克斯· 英克尔斯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受哈佛大学的资助组成了一个哈佛一斯坦福研究项目,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六个国家中访问了六千人,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调查,写成了《走向现代化》一书。日本东京大学则在1964 年举办了现代化专题讨论会,讨论了日本学者在研究现代化当中的各种概念和立场。1965 年 6 月,南朝鲜以亚洲的现代化为题,召开了有66 名国际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集中讨论了现代化的概念、亚洲的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政治、经济和人口等问题。同年 9 月尼日利亚也在伊巴丹大学召开了以政治和社会变化为题的国际会议,包括作为尼日利亚政府顾问的阿尔蒙德在内的一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讨论了现代化以及政治发展问题。而在美国,现代化的讨论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最为活跃。在 1968 年政治学会的会议中,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社会学中的社会变迁理论的风靡以及六十年代英美历史学界所开展的关于工业革命的大辩论都可以认为与现代化研究有关。此外关于现代化研究写得最好的几本著作也几乎都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出版的。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出版于 1965
年,利维的两卷本《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出版于1966 年,现任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的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一本专论政治现代化的书:《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于 1968 年,两本享有声誉的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专题论文集,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迈伦·韦纳主编的《现代化:成长的动力》和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则分别出版于 1966 年和 1976 年。
但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则不再是非常时髦的课题了。社会科学界中结构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人们发现结构方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致于在这一思潮最盛行的法国有人宣布结构主义己经死亡,现代化研究所出现的衰落可能与这种情形有点关系。同时西方学术界中新观点和新模式不断出现,也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更趋向于多样化,而不为某一种风行的理论所诱惑。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概念不断翻新的一个原困。例如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中,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逐步出现的发展问题,南北对话等,使得今天这一领域中的学者更多地采用发展理论和互相依附理论,而不再象战后那样居于世界力量和财富的首要地位,把美国视为一个完全现代化了的国家,带着傲视和怜悯的目光来看待第三世界
国家,讨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不过,尽管现代化研究不象前二十年那么风靡,但研究者依然大有人在。例如关于中国,香港大学亚洲中心于1979 年出 版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学者的研究在内的论文集《现代化在中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贝迪亚·瓦尔马在 1980 年出版的现代化研究专著《发展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一项理论研究》一书中,也专门讨论了中国的现代化。普林斯顿东亚系的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八十年代初期则写了一本颇有名气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看来现代化的研究仍旧会持续下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国家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只要现代化的确是一种存在过和正存在着的普遍进程,那么现代化研究就还会具有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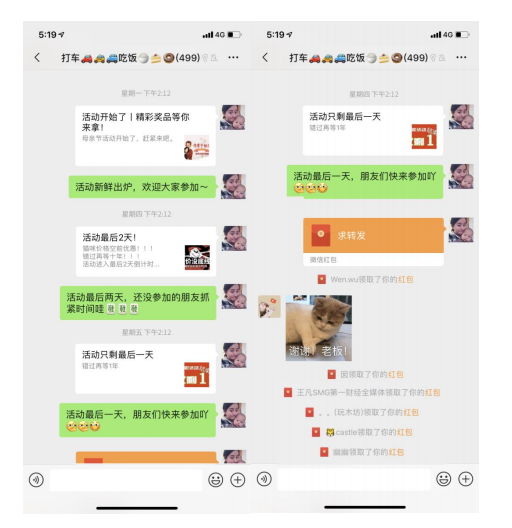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